图 | 视觉中国
(南京) 刘少勤
二哥当上爷爷了,我也跟着升格,国庆节回了趟老家庆贺。这也是母亲去世后我的首次老家之行。
节前拿到请假报告单,迟迟没有下笔。报告单上的请假事由,以往都是豪迈写上“看望母亲”“陪母亲过节”之类,“母亲”二字尽可能写得周正,生怕字写得不好会让母亲跟着变丑。今年五一节,母亲走完她83岁人生,去找老父亲了。之后五个月,我就没有再回。老家还有很多亲人,大姐,三个哥哥,还有堂哥堂姐、侄儿侄女,还有……填写请假事由时,我扭捏地写下“回老家探亲”。
2号下午出发,一家三口,儿子驾车。出发前,我竟下意识地翻出身份证,塞进包里。以前从未如此,回家嘛,当然不需出示身份证。
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。蓝天白云,一排排杨树,一片片金黄稻田,好景致。儿子心细,播放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歌。可我心神不宁,回家第一站去哪,晚饭哪吃,晚上住哪,问题萦绕脑海。我决定发个信息,请同学帮忙预订房间。正编信息,老家的大哥电话来了,说老小你真有口福,我在河里捕鱼,好几斤了,还说大嫂前天就开始收拾房间,床铺都已备好。心里好暖,给同学的信息秒删。大哥家在大山脚下,但条件不差城里别墅,当年建房时就为我安排了专门房间。也好,晚上住大哥家,第二天上午去县城看二哥的宝孙子。在老家,看望一老一小,都兴早晨或上午。心情一下子舒坦了,跟着音乐哼叽。
人车欢快前行。二哥来电话了,视频,一脸的汗,他刚赶到县城的新家,叫我们去吃晚饭。我强调老家风俗,说看宝宝应该是上午,晚上去不方便。他说,那是指外人,家里人,随时随地,半夜三更都行。
二哥新家在四楼,面积不小。看过小宝宝,粉嘟嘟的,酣睡中,不时抿着小嘴作喝奶状。晚饭安排在饭店,满桌子菜。饭后,二哥二嫂再三留我住下来,我坚持要回大哥家,父母不在了,长哥为父、长嫂为母,更重要的是,大哥家与母亲生前住的宅子紧挨着。五个月都没进母亲房间了,想啊。
晚上9点多,快到家了,我和妻提前下车走走。熟悉的路,熟悉的树,熟悉的虫鸣,熟悉的空气味道,还有熟悉的满天星斗。到家门口了,首先迎接的是那棵百年老桂,老桂每年都要连开两茬,第一茬还未谢尽,枝头缀着残花,稍一碰触就雨般落下。我和老桂都知道,这些年来,母亲多少次树下翘首迎我归来,多少次抹泪送我远行。但只有老桂知道,每次送我离家后,瘦小的母亲会在树下站立徘徊多久。老桂肯定不会忘记,出殡那天,母亲的遗体安放树下,黄绸布盖着她干枯的身骨,树冠像一把大伞最后一次为她遮挡风尘,我泪眼婆娑看她上了灵车,怀抱遗像领她从树下出发,永远离开了曾经塞满五个子女吵闹和欢笑的家。此刻,母亲的房门紧锁着,窗玻璃映着星光,里面一团漆黑,一片寂静。要是以前,我会贴着门窗听母亲的呼噜,会叫喊几声,会敲门进入,会与母亲好一阵子唠嗑。对于一个中年男人,当他回到久别的家,能够豪迈甚至粗鲁地叫几声“娘”,能够听到声音或高或低的回应,该是何等的幸福!
第二天一早,我起床直奔母亲的房间。门已打开,里面摆放着新床新柜,一股新家具特有的气味粗暴地驱赶早晨空气的清新,母亲的气息早已荡然无存。三哥腿脚不便,他准备住到一楼母亲的房间。母亲生前用的桌椅搬到屋外,我怔怔地盯着它们,抚摸着,手上沾满泪珠般的晨露。堂哥堂姐看到我,热情地招呼我去喝茶、吃早饭,亲切都写在彼此脸上。我想去墓地看看母亲,大哥不许,不是清明冬至,不要随便打扰。
姐姐家是必去的,半晌时赶了过去。她瘦了,我们聊了好一阵子,就是没有谈及母亲。姐说上午来不及准备,让我隔天中午或晚上去吃饭。我笑说,我想午饭晚饭连着吃。她也笑了,说吃十餐八餐都行。
再次回到母亲的房间。这里已是三哥的新家,若干年后,它又将是侄女儿魂牵梦绕的老家。下午,我执意回南京,哥嫂将车厢装满南瓜、地瓜、玉米棒和青菜,堂姐在家扑腾得鸡飞狗跳,非要抓只鸡鸭给我……
母亲离开后我第一次回老家,前后不到24小时。
送走老母亲,又迎来一个小可爱。自然世界是总体平衡的,我的内心世界也日渐平衡、越发笃定。面对悲欢离合和进退得失,我有自己的支点和方向。
父母亲走了,我在心底给他们安个家。在二老看护下,我好好干工作,好好过日子,全家都开开心心的。有空,也会常回老家看看,山脚下田埂上有我童年脚印,门口小河上有我架起的小桥,三乡五里有我一拨亲人、一群好友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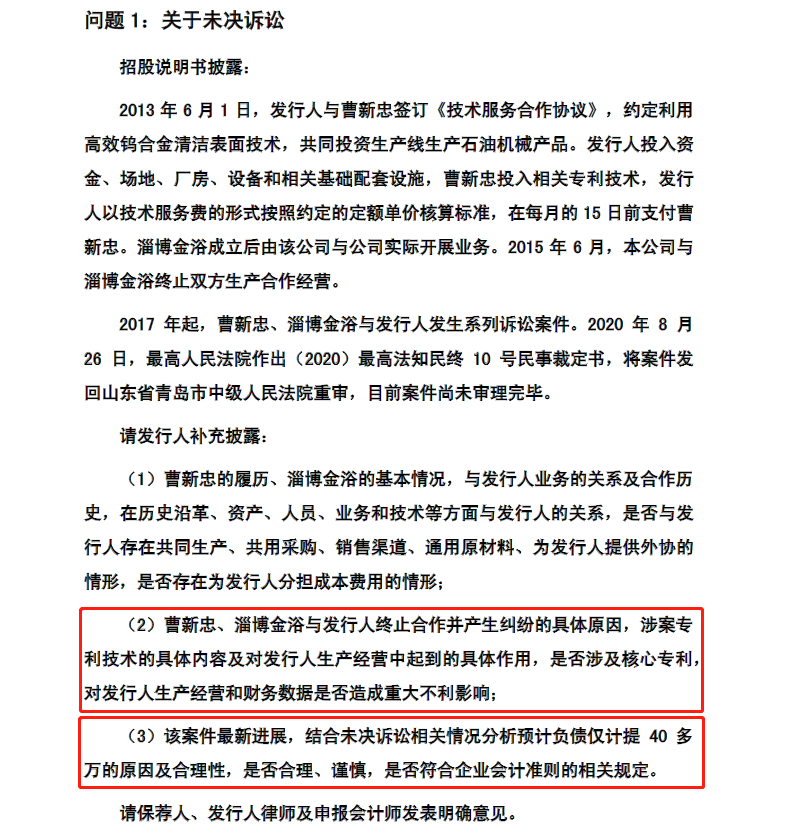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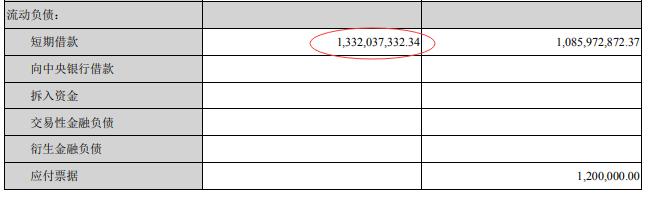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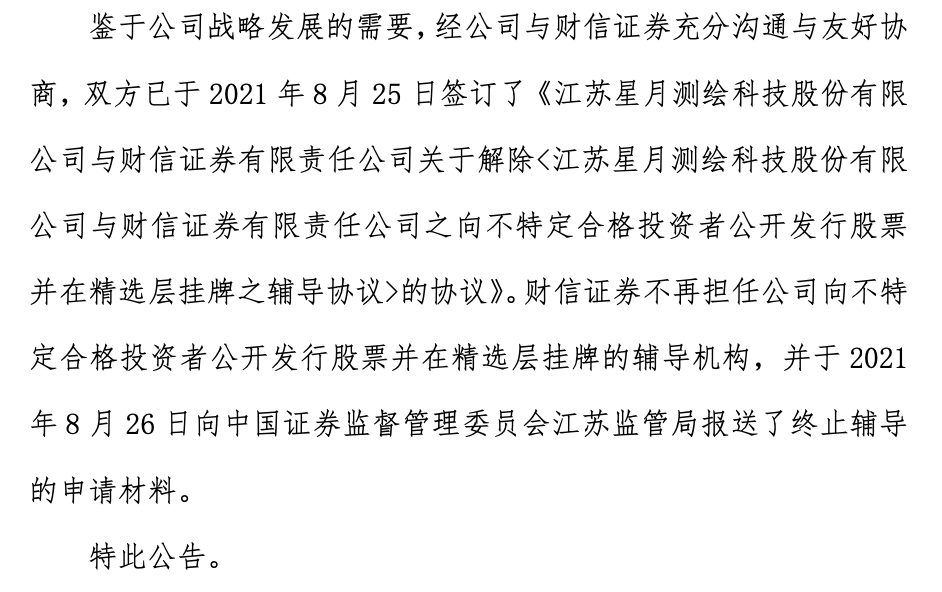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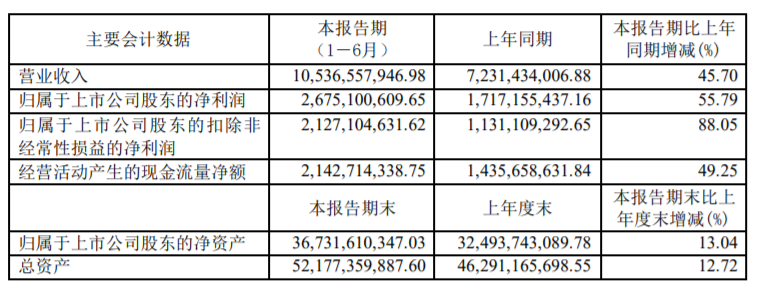



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